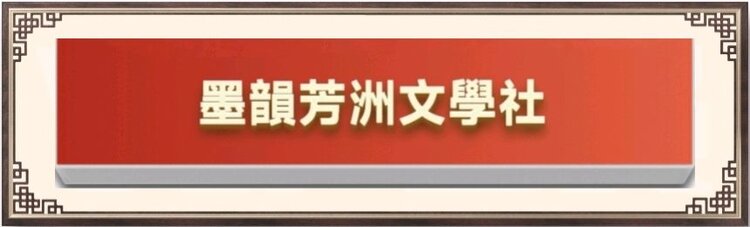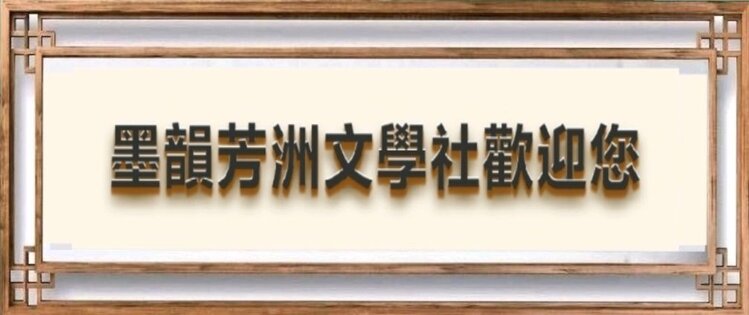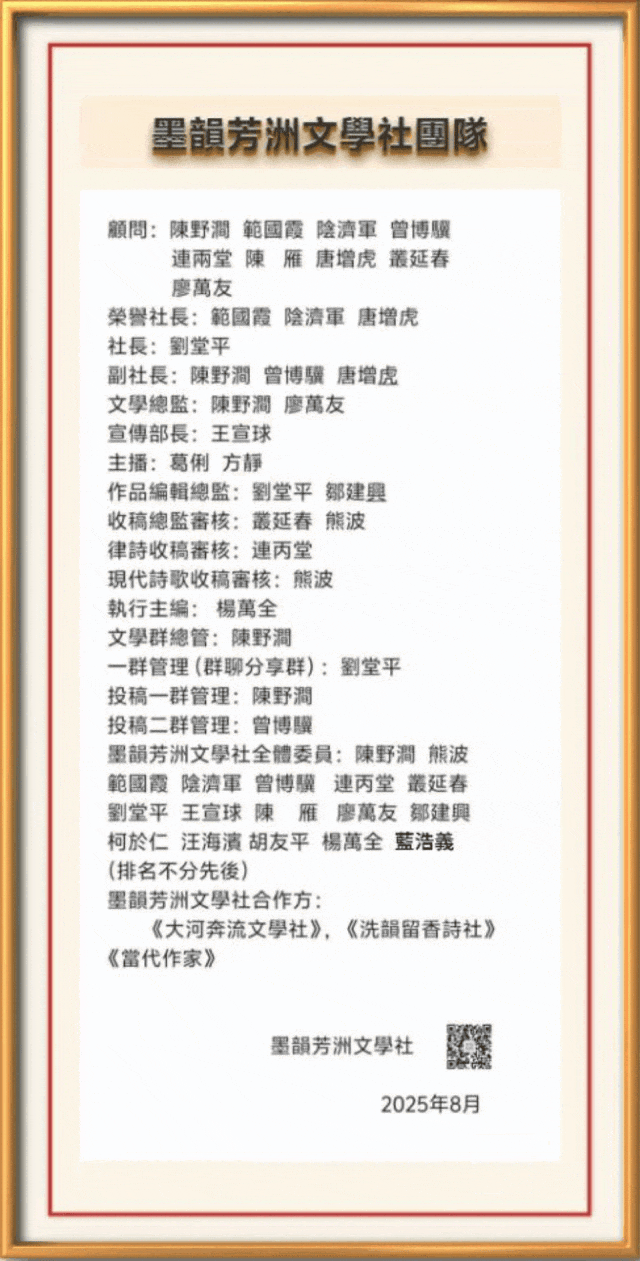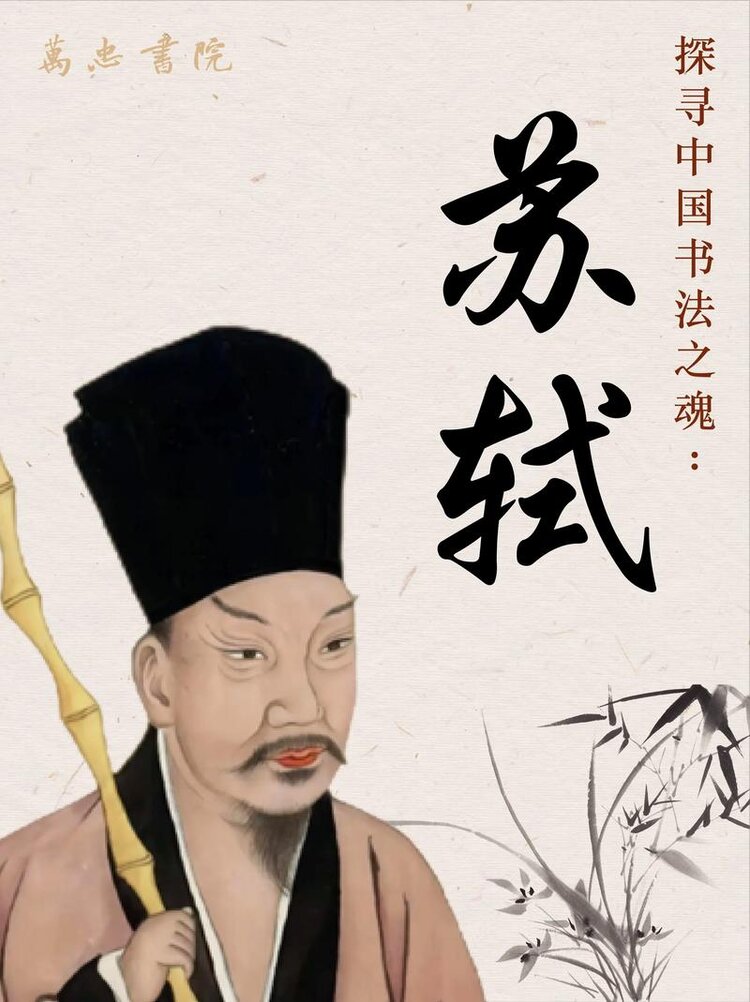唐宋八大家之苏轼
文/向思刚(湖北)
散文·一蓑烟雨任平生
苏轼(1037年-1101年),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,眉州眉山人,北宋文坛冠冕。与其父苏洵、其弟苏辙并称“三苏”。少年得志时,他是欧阳修眼中“当避此人出一头地”的文坛新星,笔尖流淌着“奋厉有当世志”的锐气;乌台诗案后,半生如蓬草飘零,黄州的雨、惠州的荔、儋州的桄榔,却将他的才情淬成了旷达的青铜。从朝堂才子到“坡仙”,他用一生证明:苦难从不是生命的终章,而是精神的炼金炉。
眉山的灵秀孕出他的锋芒。二十一岁赴京应试,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让欧阳修拍案——“老夫当避路,放他出一头地也”。彼时的苏轼,如春日纸鸢,东风助势便要直上青云。可命运偏要在他最顺遂时扯断丝线:乌台诗案的罗网骤降,御史台的牢狱里,一百三十个日夜的幽暗,让“是处青山可埋骨”的绝命诗沾了血痕。幸得亲友力保,贬谪黄州成了死里逃生的恩典,这方长江边的小城,就此成了他生命的熔炉。
初到黄州,定惠院的荒屋漏雨,他自嘲“黄州真在井底”。昔日握笔的手,第一次扶起犁铧,在东坡的泥土里翻出深浅的沟壑。汗滴坠进田垄时,他忽然懂了:庙堂的高阁会倾,而大地永远托举着生灵。于是有了“东坡居士”的别号,像给漂泊的灵魂找了个锚点——此后无论漂到哪里,这两个字都是他与大地签订的契约。
黄州四年,是灵魂在苦水里泡透又绽开的四年。寒食节的雨下得绵密,小屋像浮在水面的渔舟,灶冷如冰,病骨支离。他提笔写《黄州寒食诗帖》,墨色先重后轻,笔锋由滞转狂:起笔是“自我来黄州,已过三寒食”的沉郁,中段是“空庖煮寒菜,破灶烧湿苇”的窘迫,末了忽作“也拟哭途穷,死灰吹不起”的枯寂——那不是技巧的炫技,是生命在绝境里的喘息,每一道飞白都带着骨头摩擦的声响。这幅“天下第三行书”,原是苦难刻在纸上的年轮。
而赤壁的月夜,让他把苦难酿成了酒。泛舟江上,洞箫声里生出“哀吾生之须臾”的怅惘,却在“逝者如斯,而未尝往也”的顿悟中释然。原来江上清风、山间明月,本就是造物者的无尽藏——何必争一时得失?前后《赤壁赋》如双璧,将个人悲欢沉入宇宙洪流,苦难便成了观照永恒的窗口。那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吟啸,从此成了无数失意者的精神蓑衣。
命运总爱把最烈的酒留给通透的人。惠州的瘴气里,他嚼着荔枝笑“不辞长作岭南人”;儋州的桄榔林下,他结庐办学,教黎民子弟识字,说“我本儋耳人,寄生西蜀州”。当他在蛮荒之地凿出第一口井,当他把中原文化的火种播进椰林,苦难早已不是枷锁,而是让生命根系扎得更深的养分。
千年后再读苏轼,读的从来不是诗文,而是一种活法:不是躲雨,是雨中吟啸;不是怨命,是与命共舞。他的赤壁月仍照今人,他的蓑衣仍护着每个在风雨里前行的人。正如他临终前那句“着力即差”——真正的旷达,从不是硬撑的坚强,而是看透世事后,依然保有对生命的热望。这或许就是他留给人间的礼物:让每个受过伤的灵魂,都敢在雨里说“任平生”。